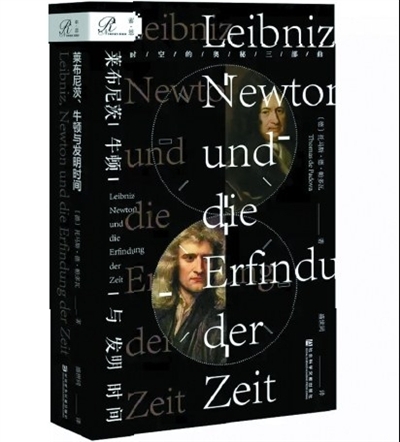時(shí)間這個(gè)概念,最早來源于大自然。日出日落,星辰流轉(zhuǎn),四季變換,都意味著時(shí)間。然而,在我們的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中,時(shí)間早就已經(jīng)超出了它在各種自然現(xiàn)象中的意義,現(xiàn)代人的生活其實(shí)是被“時(shí)鐘”所支配的。
這種超越自然的“時(shí)間”概念是怎么形成的?這種嶄新的時(shí)間概念又是怎樣影響人類社會(huì)的?德國科普作家和科學(xué)史家托馬斯·德·帕多瓦在《萊布尼茨、牛頓與發(fā)明時(shí)間》中,通過萊布尼茨和牛頓兩位科學(xué)家的經(jīng)歷,串聯(lián)起了一段關(guān)于“時(shí)間”的精彩歷史。
正是因?yàn)橛辛诵碌臅r(shí)間概念,我們才能走進(jìn)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。時(shí)間這個(gè)概念形成的歷史,是一段科學(xué)史,也是人類社會(huì)發(fā)展的歷史。
A 時(shí)間成了公共品
鐘表時(shí)間進(jìn)入城市生活的每一個(gè)角落,激發(fā)了科學(xué)的火花,改變了社會(huì)的面貌,重構(gòu)了人與時(shí)間的關(guān)系,推動(dòng)了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本質(zhì)的思考
太陽、流水、鐘聲都是時(shí)間的象征,那么,我們所說的“時(shí)間”到底是什么?如果說時(shí)間是被發(fā)明的,我們可能會(huì)驚訝,日升月落,難道不是自然規(guī)律嗎?
要知道這個(gè)答案,首先要了解在精確的鐘表發(fā)明之前,那時(shí)候的人類是如何認(rèn)識時(shí)間的,他們是怎樣生活的。
最早,人類對時(shí)間的認(rèn)識來源于對自然的觀察。天體運(yùn)動(dòng)造就了晝夜、月相和季節(jié)等,它們有著近似固定的周期,人們的生活也就形成了與之和諧的節(jié)律。
在17世紀(jì)初的歐洲,農(nóng)業(yè)依然占據(jù)著重要的地位,根據(jù)日出日落和季節(jié)更替,人們進(jìn)行播種、培育和收割,如果一個(gè)社會(huì)停留在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,這樣的時(shí)間概念其實(shí)也就夠用了。
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歐洲,盡管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很多非常昂貴的鐘表,但這些鐘表都沒有分針和秒針,只能像中國古代計(jì)時(shí)那樣大致知道是“午時(shí)三刻”,是一種模糊的時(shí)間。牛頓作為一個(gè)牧羊人的后代,在小的時(shí)候,經(jīng)常觀察在一天當(dāng)中,影子的方向和長度是如何變化的,這完全是一種與傳統(tǒng)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相適應(yīng)的時(shí)間觀念。
然而,17世紀(jì)末18世紀(jì)初的歐洲,發(fā)生了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,城市居民的生活在這個(gè)時(shí)期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在這場即將發(fā)生的社會(huì)變革中,扮演重要角色的,就是精確的鐘表。
1583年,伽利略發(fā)現(xiàn)了擺的等時(shí)性——擺的周期與擺長的平方根成正比。利用該原理,惠更斯于1657年制作了擺鐘,又于1675年發(fā)明了擺輪游絲。這不僅使機(jī)械鐘的誤差減少至每天1分鐘以內(nèi),也為便攜式鐘表的誕生鋪平了道路。新式鐘表結(jié)合了兩種時(shí)間觀念:指針的運(yùn)動(dòng)既模擬循環(huán),也呈現(xiàn)流逝,時(shí)間單位從一刻鐘精確到分,然后到秒。此后數(shù)十年間,它開啟了一場影響深遠(yuǎn)的時(shí)間革命:鐘表時(shí)間進(jìn)入城市生活的每一個(gè)角落,激發(fā)了科學(xué)的火花,改變了社會(huì)的面貌,重構(gòu)了人與時(shí)間的關(guān)系,推動(dòng)了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本質(zhì)的思考。
托馬斯·德·帕多瓦認(rèn)為:“從我們的時(shí)間文化來看,17世紀(jì)可謂設(shè)置了全新的標(biāo)準(zhǔn)。”客觀、數(shù)學(xué)的鐘表時(shí)間不僅改變了日常生活,也沖擊著原有的社會(huì)結(jié)構(gòu),打破了君主和教會(huì)對時(shí)間制度的壟斷。隨著私人鐘表的普及,時(shí)間成為公共品,進(jìn)而推動(dòng)了個(gè)體意識的覺醒。
鐘表的誕生,還促進(jìn)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(dòng)的發(fā)展,給當(dāng)時(shí)的歐洲人帶來了全新的時(shí)間概念,人們開始有了“守時(shí)”的觀念,工人們開始按時(shí)上下班,而且每天工作的時(shí)間也越來越長,開始從農(nóng)業(yè)時(shí)代即將進(jìn)入工業(yè)時(shí)代。而新型航海鐘的發(fā)明,把海洋上的時(shí)間測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,徹底解決了遠(yuǎn)洋航海中的定位問題。這為后來英國的海上霸權(quán),以及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(qū)的殖民提供了技術(shù)基礎(chǔ)。
B 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的恩怨糾葛
近代以來的任何重大科學(xué)成果都不是某人被蘋果砸中后的靈光乍現(xiàn),而是歷代知識的積累、傳承和發(fā)展,是跨國交流與合作的結(jié)晶
既然本書叫作《萊布尼茨、牛頓與發(fā)明時(shí)間》,萊布尼茨、牛頓以及兩人之間的恩怨糾葛自然是書中提到的重點(diǎn)內(nèi)容。不過,這個(gè)有些老生常談的故事,在托馬斯·德·帕多瓦筆下,卻有了生機(jī)。他運(yùn)用多線敘事手法,將兩人的經(jīng)歷與重大歷史事件相交織,體現(xiàn)了300多年前西歐社會(huì)的動(dòng)蕩、變革與發(fā)展,主題圍繞的還是——時(shí)間。
在牛頓的物理學(xué)中,時(shí)間是一條持續(xù)不斷的水流。牛頓的絕對時(shí)間論在他的《自然哲學(xué)的數(shù)學(xué)原理》中是這樣描述的:“絕對的、真實(shí)的和數(shù)學(xué)的時(shí)間,由于它的自然本性,不受外界影響而穩(wěn)定地流逝,換種說法是持續(xù)不斷地流逝。”同樣,他對空間的看法也寫入書中,“絕對空間由于自然本性,在不與外部事物發(fā)生關(guān)系的情況下總是不變和不能移動(dòng)的”。
我們在日常生活中,不知不覺都在采用牛頓的這種時(shí)間觀。比如,你和朋友說:“今天晚上七時(shí)半一起吃飯。”這句話里就包含著牛頓的時(shí)間觀,我們似乎天然就假設(shè),已經(jīng)有了一個(gè)固定的時(shí)間背景存在,不會(huì)因?yàn)楝F(xiàn)在是夏天,七時(shí)半就變得比較晚;不會(huì)因?yàn)槭嵌欤邥r(shí)半就變得比較早;也不會(huì)因?yàn)槟阍诔燥垼瑫r(shí)間就過得比較快。“晚上七時(shí)半一起吃飯”這個(gè)約定可以成立,就是因?yàn)闀r(shí)間成了一個(gè)絕對的概念。
牛頓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和空間的絕對論是基于17世紀(jì)人類對周圍空間物體觀察的結(jié)果,也是基于17世紀(jì)人類能夠?qū)嵤┑目茖W(xué)實(shí)驗(yàn)的結(jié)果。在牛頓去世100多年后的1890年,世界標(biāo)準(zhǔn)時(shí)間的倡導(dǎo)者、加拿大測繪工程師桑德福·弗萊明也成了絕對時(shí)間論的追隨者。他在1890年撰寫的文章《落伍的古代計(jì)時(shí)方法》中說:“時(shí)間不受物質(zhì)、空間或距離的影響。它是普遍而非地區(qū)性的,它是絕對的單一,整個(gè)宇宙都一致。”
然而,跟牛頓同一時(shí)期的科學(xué)家萊布尼茨,卻從純理性的角度,提出了對時(shí)間概念的另一種全新的理解,他的觀點(diǎn)還和牛頓針鋒相對。萊布尼茨認(rèn)為,宇宙中沒有一種絕對的時(shí)間秩序,時(shí)間是一種“思想物”,它不能脫離我們的意識存在。
有時(shí)候,我們也會(huì)用萊布尼茨的思路來理解時(shí)間的概念。比如,我們可能會(huì)和同事說:“下班后一起去吃飯。”這句話里聽起來沒有任何的時(shí)間信息,我們完全不知道“下班之后”這個(gè)時(shí)間到底是在下午五時(shí)、六時(shí),還是晚上的八時(shí)、九時(shí),但這句話的意思是很明確的。我們能夠感受到時(shí)間的流逝,就是因?yàn)槲覀円恢鄙钤谟梢蚬P(guān)系構(gòu)成的網(wǎng)絡(luò)之中。
然而,遺憾的是,兩個(gè)未能殊途同歸的偉大靈魂從未謀面,也并沒有公開地為自己辯論。因?yàn)椋瑹o論在學(xué)界還是仕途,牛頓都更加符合“成功”的標(biāo)準(zhǔn),所以萊布尼茨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的理論,長期被嚴(yán)重忽視。就像托馬斯·德·帕多瓦所說,萊布尼茨的這種對于時(shí)間的理解一直處在牛頓物理學(xué)的陰影之下。盡管有許多哲學(xué)家非常關(guān)注萊布尼茨的觀點(diǎn),但這種思想沒有能夠影響科學(xué)界,所以很快就被遺忘了。
事實(shí)上,近代以來的任何重大科學(xué)成果都不是被蘋果砸中后的靈光乍現(xiàn),而是歷代知識的積累、傳承和發(fā)展,是跨國交流與合作的結(jié)晶——開放帶來進(jìn)步,封閉必然落后。在全球聯(lián)動(dòng)日益緊密而科技壁壘可能被重新筑起的今天,這樣的信念尤為珍貴。
C 時(shí)間是我們思考的方式
只要大統(tǒng)一理論尚未建立,物理世界的終極圖景沒有展開,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的討論就不會(huì)結(jié)束——也許永遠(yuǎn)都不會(huì)結(jié)束
盡管牛頓的觀點(diǎn)看似更被人們接受,可是到了20世紀(jì),科學(xué)家們卻拋棄了牛頓的時(shí)間觀念,開始擁抱萊布尼茨所定義的“時(shí)間”。
19世紀(jì)末,人類全面突破自身經(jīng)驗(yàn)的維度,哲學(xué)和科學(xué)界才重新發(fā)現(xiàn)關(guān)系主義的價(jià)值。
柏格森拒絕了時(shí)間的實(shí)體化和空間化,取消了過去、現(xiàn)在和未來的藩籬,將時(shí)間統(tǒng)一到綿延。在科學(xué)領(lǐng)域,恩斯特·馬赫率先批判了水桶實(shí)驗(yàn),否定了相對于絕對空間的絕對運(yùn)動(dòng)的存在。接著,愛因斯坦基于光速不變原理提出了狹義相對論,致使時(shí)間和空間不再相互獨(dú)立,而是被統(tǒng)一為“四維時(shí)空”。1915年,愛因斯坦又在廣義相對論中進(jìn)一步指出,運(yùn)動(dòng)的同時(shí)性是相對的,每個(gè)觀察者都能測得特殊的“原時(shí)”。不存在絕對的參考系,“空間和時(shí)間只是我們進(jìn)行思考的方式”。
相對論帶來的這種全新的“時(shí)間”概念也反過來帶來了技術(shù)上的重大突破。我們生活中到處都有相對論所帶來的影響。比如,人們現(xiàn)在每天使用的GPS定位上,也用到了相對論的時(shí)間修正。根據(jù)狹義相對論,高速運(yùn)動(dòng)衛(wèi)星上的原子鐘每天要比地球上的鐘慢7微秒,而如果再進(jìn)一步考慮廣義相對論,衛(wèi)星上的時(shí)鐘又會(huì)比地球快45微秒。可能你會(huì)覺得這些誤差太小了,比我們“一眨眼”的時(shí)間還快。可是,這種誤差如果不進(jìn)行修正的話,那么GPS系統(tǒng)的定位每天將會(huì)累積大約10公里的誤差。從GPS這個(gè)例子中,我們看到了技術(shù)跟科學(xué)之間的復(fù)雜互動(dòng)。技術(shù)對科學(xué)提出了要求,而只有當(dāng)科學(xué)達(dá)到一定的程度,技術(shù)的實(shí)現(xiàn)才有可能。
你可能沒法想象,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的發(fā)明,會(huì)對人類產(chǎn)生如此巨大的影響;而隨著科學(xué)的發(fā)展,我們得以從更多的角度認(rèn)識時(shí)間。正如本書譯者在序言中提到,它或許是物質(zhì)運(yùn)動(dòng)或能量傳遞的方式——根據(jù)熱力學(xué)第二定律,時(shí)間在大爆炸之前或熱寂之后都不存在;又或許是生命意識的反映——心理學(xué)認(rèn)為,我們所感受的“現(xiàn)在”不過是一段最多兩三秒的時(shí)長。今天,雖然世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無法擺脫對絕對時(shí)間的想象,但已經(jīng)傾向于認(rèn)為,關(guān)系主義更接近時(shí)間的本質(zhì)。然而,只要大統(tǒng)一理論尚未建立,物理世界的終極圖景沒有展開,關(guān)于時(shí)間的討論就不會(huì)結(jié)束——也許永遠(yuǎn)都不會(huì)結(jié)束。
至少,在此之前,托馬斯·德·帕多瓦講述的故事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時(shí)間經(jīng)驗(yàn)、時(shí)間工具和時(shí)間觀念,思考現(xiàn)代時(shí)間的“發(fā)明”及結(jié)果。如此,置身于躁動(dòng)的時(shí)間之網(wǎng),我們就能少一點(diǎn)無措和迷茫,多一分自信與堅(jiān)強(qiáng)。(咸寧日報(bào)綜合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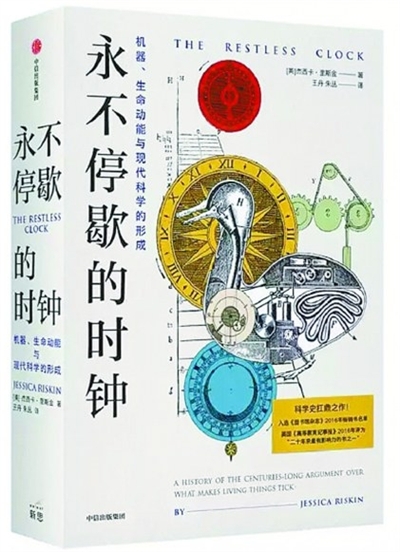





 2025-03-27
2025-03-27
 2025-03-27
2025-03-27